结束语 | 愿你能做一个真正“懂”的程序员
周爱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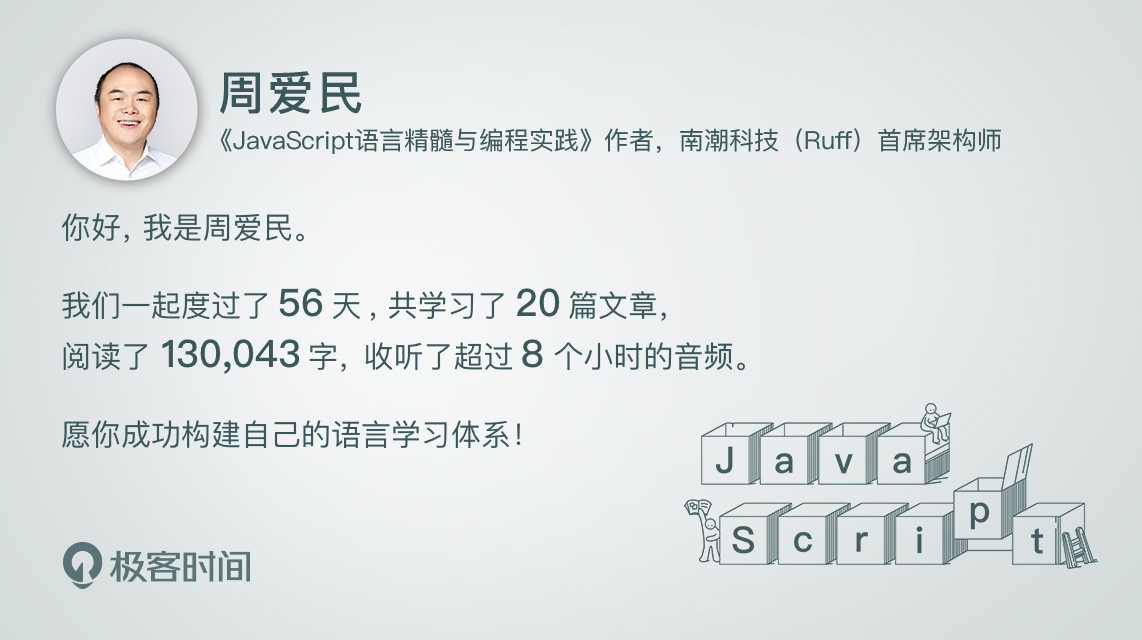
该思维导图由 AI 生成,仅供参考
我常常讲一个比喻,这个比喻是说有一座塔,塔门口有两尊石狮子。
如果有人登塔,那么进塔之前他固然是会看到这个狮子的,往上走,正好到塔后,石狮子就没有了,于是这个人说“就我一楼之所见,没有狮子”;绕到前面,一看,石狮子好好地在那儿,于是这个人又说“于我所见,有狮子”。如此行至二楼,他又会说“没有狮子”,而后又否定说“真真切切是有狮子在的”。
对于旁人来说:只听这个人讲“有,或没有”狮子,会知道他在几楼吗?又或者说,就算知道这个人在几楼,又能知道他说“有,或没有”狮子,是综览事实之所见,还是未见事实全貌时的一时所言?你其实并不知道。
我们只是要么相信了对方所在的高度,要么认可了对方所言的真假。而大多数时候,我们其实无从判断:那个人说的是不是对的,又或者他说的,究竟是在几层楼上看见的石狮子。
每一层可见的狮子,都是相同的狮子;但每一次的所见,却不相同。同样是真理,在初学者和大师的口中说出来,尽管字面上都是一样的,但是却包含着不同高度的理解。所谓大师,也不过是先行者,只是他处在的楼层,决定了他看得见下面所有的层次上的真相,也辨得清每一层所见的石狮子的样子。
所以,所谓“懂”,其实说的不是一个结果,而是一个状态:知道自己所在之位置的,才是真的懂;知道自己所见之局限的,才是真的懂;知道自己所向之湮远的,才是真的懂。
公开
同步至部落
取消
完成
0/2000
笔记
复制
AI
- 深入了解
- 翻译
- 解释
- 总结

这篇文章以“愿你能做一个真正‘懂’的程序员”为题,通过塔楼和石狮子的比喻,阐述了程序员在技术领域中的认知和理解。作者强调了“懂”并非结果,而是一个状态,需要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、所见的局限,并且思考才是进步的本质。文章指出,对于程序员来说,理解技术需要不断积累知识、形成结构和体系,并且不固执于已见,而是不断进步。作者还分享了自己在技术领域的经历和思考,鼓励读者成为真正“懂”的程序员。文章内容深刻,引人深思,对于技术人员来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。
仅可试看部分内容,如需阅读全部内容,请付费购买文章所属专栏
《JavaScript 核心原理解析》,新⼈⾸单¥59
《JavaScript 核心原理解析》,新⼈⾸单¥59
立即购买
登录 后留言
全部留言(20)
- 最新
- 精选
- Geek_7bfb5b老师讲的很好, 老师后续还会出其他相关的课程吗? 期待, 谢谢。🙏
作者回复: 谢谢支持。^^. 计划里面,这个课程是还有个续篇的,也应该是在20讲左右。不过确实时间没定,所以极客时间也不让公开~~ 其它方面的课程,目前还没想过,时间上排不开呢,毕竟我不是专职来做教育的,做太多课程,非我所能。:(~
2020-01-0915  潇潇雨歇2020,再学一遍专栏。
潇潇雨歇2020,再学一遍专栏。作者回复: 👍+3
2020-01-068 亦枫丶从前几节课的疑惑,到后面几节课的承上启下,再到最后的浑然一体,这门课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,也让我学到了体系,见识到了不一样的学习角度,老师真实让我大开眼界。 老师的文字如艺术品般,印证了那句“好的东西都是美的”。 谢谢老师
亦枫丶从前几节课的疑惑,到后面几节课的承上启下,再到最后的浑然一体,这门课不仅让我学到了知识,也让我学到了体系,见识到了不一样的学习角度,老师真实让我大开眼界。 老师的文字如艺术品般,印证了那句“好的东西都是美的”。 谢谢老师作者回复: 😄多谢多谢。 我需要继续努力做得更好💪
2020-01-073 墨灵真的非常希望看到周爱民老师的后续的专栏,这个专栏是越品越有味。
墨灵真的非常希望看到周爱民老师的后续的专栏,这个专栏是越品越有味。作者回复: 我当努力搞定之💪
2020-04-092 晓小东老师,你的下一课程啥时候出啊,有点等不及了
晓小东老师,你的下一课程啥时候出啊,有点等不及了作者回复: 这个……我说了作不得准呀。^^.
2020-01-112 行问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,又是否理解这其中的用意。 不止是注意到了,也领悟到了。
行问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,又是否理解这其中的用意。 不止是注意到了,也领悟到了。作者回复: 😄
2020-01-062- Geek_885849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,这课我听了不下5遍,每次感觉都有新的收获,市面上的书基本都是讲语法,没有这种深度的解析,期待老师后续的课程
作者回复: 谢谢。 这本新书应该是你需要的: https://item.jd.com/12883028.html
2020-08-061  天魔狂戦谢谢爱民老师,课程看了一遍,懂一些,又不懂了一些,之后再读一遍应该会有更多收获~
天魔狂戦谢谢爱民老师,课程看了一遍,懂一些,又不懂了一些,之后再读一遍应该会有更多收获~作者回复: 努力~ :)
2020-06-201 .Alter第一遍学完啦,虽然有的章节还是一头雾水,但也是收获颇丰。感谢老师的分享,引领我们思考、建立体系!期待老师的后续课程 O(∩_∩)O
.Alter第一遍学完啦,虽然有的章节还是一头雾水,但也是收获颇丰。感谢老师的分享,引领我们思考、建立体系!期待老师的后续课程 O(∩_∩)O作者回复: 谢谢。一齐努力!^^.
2020-02-171 水木年华这个专栏真不是一两遍就能弄明白的, 我会时不时的翻阅。 谢谢周老师提供这么好的课程。
水木年华这个专栏真不是一两遍就能弄明白的, 我会时不时的翻阅。 谢谢周老师提供这么好的课程。作者回复: ^^.
2020-01-121
收起评论